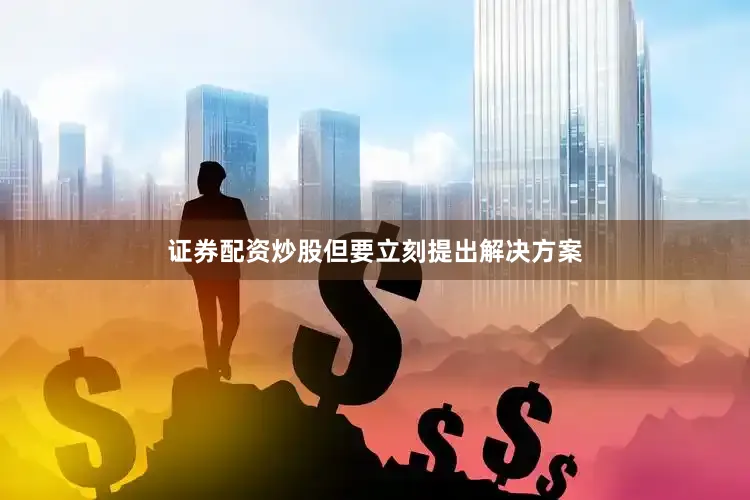
同治十二年,暮春。
江宁藩署,西花厅。
陈伯安的手指轻轻抚过桌上的辞呈,指尖摩挲着那句“二十载寄食幕府,寸功未立,愧对恩师”。
他知道,这封信意味着他半生的心血与忠诚,即将化为一缕轻烟,消散在晚清的权力场中。
他辅佐曾国藩二十年,从京城到湘江,从金陵到直隶。
他设计过军械,测算过漕运,甚至连曾国藩的家书,都经他润色。
可他终究只是个幕僚,一个没有品级的“白衣宰相”。
而此刻,在天津的李鸿章,正凝视着一张关于机器改进的草图,心头巨震。
他知道,一个被时代埋没的绝世人才,正打算悄然归隐。
他必须阻止。

01
陈伯安是带着一丝萧索走进西花厅的。
他今年五十八岁,鬓角已经斑白,但身形依旧挺拔,一双眼睛里,带着经年累月浸润书卷的清明与洞察。
他将辞呈恭敬地放在了曾国藩的书案上。
“伯安,你这是何意?”曾国藩正批阅着奏折,抬起头,语气平静,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。
曾国藩知道陈伯安的心结。
陈伯安是他幕府中资历最老、学问最杂、见识最广的一位。
说他学问杂,是因为他不仅精通儒家典籍、兵法韬略,更对那些被清流们斥为“奇技淫巧”的格物之学——如算术、几何、火器、机器——有着深入的研究。
在湘军初创时期,陈伯安曾为曾国藩设计了简易的火炮射程计算法,大大提高了湘军火器的命中率。
在平定太平天国后,他更是为曾国藩主持的江南制造局,提供了最初的选址和规划。
论功绩,陈伯安早就该入朝为官,哪怕是外放知县,也绰绰有余。
但二十年过去了,他依然是曾国藩身边一个没有品级的幕僚。
“恩师,”陈伯安的声音有些沙哑,“学生已经老了,心力不济。二十年未获一职,学生也明白,不是恩师不愿提携,而是学生这秉性,实在不适官场。”
陈伯安的秉性,确实是他在官场上最大的阻碍。
他清高,不屑于与官场上的衮衮诸公周旋。
他务实,厌恶空谈心性、不理实务的清流。
更要命的是,他对于“洋务”的热衷,让他在许多守旧派眼中,成了异类。
曾国藩沉默了片刻,拿起那封辞呈,轻轻叹了口气。
“伯安,你可知,这些年来,朝廷弹劾为师的奏折里,总有那么几句,是针对你对机器、火器的执念?”曾国藩放下奏折,揉了揉眉心。
他不是不想给陈伯安实职。
他曾试着举荐过几次,结果都被京城官僚以“此人好洋务,恐非正道”的理由驳回。
曾国藩晚年求稳,不愿为了一个幕僚,掀起太大的风波。
“学生明白,恩师爱惜羽翼,更要顾全大局。”陈伯安淡淡地说,语气中没有怨怼,只有认命。
“罢了,既然你心意已决,为师也不强留。”曾国藩将辞呈收好,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。
“这是你这二十年的俸禄和一些积蓄,你收好。”
陈伯安推辞:“恩师厚待,学生不敢收。”
“这与厚待无关,这是你应得的。你为湘军、为洋务所做的实事,远超这银两的价值。”曾国藩坚持。
“不过,在归乡之前,为师还有一事相托。”
陈伯安立刻拱手:“恩师请讲,学生鞠躬尽瘁。”
“江南制造局自开办以来,积累了大量的图纸和文献。有些是成功的,有些是失败的。你对格物之学最有心得,可否代为师,将这些图纸整理一遍,分门别类,把那些‘废弃’的图纸也一并归档。将来,或许对后来者有益。”
这听起来像是一件极其枯燥的“扫尾”工作。
但陈伯安却眼睛一亮。
他知道,曾国藩这是给了他一个最后接触“实学”的机会。
他点头:“学生遵命。”
02
江南制造局,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基石之一。
这里充斥着蒸汽机的轰鸣声、铁锤的敲击声,以及一股浓烈的煤油和钢铁混合的味道。
对于陈伯安来说,这里比戒备森严的藩署更让他心安。
他被安排在制造局一处偏僻的档案室,四周堆满了从英国、德国、美国进口的机器图纸,以及中方技术人员在仿制过程中留下的草稿和失败品。
这批“废弃图纸”数量庞大,许多图纸因为失败而被随意丢弃,甚至有些被老鼠啃噬,污迹斑斑。
制造局的官员们觉得曾国藩让陈伯安做这个工作,简直是杀鸡用牛刀。
一个资深幕僚,干着文书的活计。
但陈伯安却甘之如饴。
他每天清晨准时来到档案室,像一个饥渴的学徒,钻研着这些被时代遗弃的智慧。
“这张图纸,是仿制德式火炮的底座设计……”
“不对,这里的承重结构有明显的冗余,浪费了大量的生铁。”
陈伯安一边整理,一边进行着详细的批注。
他发现,洋务运动初期,最大的问题并非技术落后,而是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。
许多技术人员只是照猫画虎,没有理解图纸背后的力学和材料学原理。
他尤其关注那些失败的图纸。
在其中一张关于“蒸汽机活塞连杆”的设计草图上,陈伯安停了下来。
这是制造局仿制一艘小型军舰引擎时的失败品。
当时的工匠认为,连杆断裂是由于材料强度不够。
但陈伯安却不这么认为。
他拿出纸笔,在草图的角落,用娟秀但精准的墨迹写下:
“此处应为应力集中点。连杆断裂,非材之过,乃几何结构之误也。若将连接处倒圆角,并适当增加厚度,可有效分散拉应力。此为西洋‘材料力学’之精要,不可不察。”
他不仅仅是整理,他是在利用自己二十年来在军械、水利工程中积累的实学经验,给这些失败的设计“看病”。
他将自己认为可行的修正方案,详细地批注在了图纸的空白处。
他知道,自己已经决定归隐,这些批注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看到。
但这是一种习惯,也是他对“实学”的最后一份敬意。
他像一个雕刻家,在即将被尘封的石碑上,刻下了自己最后的思想印记。

03
陈伯安在制造局工作了半个月。
他整理出了上千张图纸,并且给至少三分之一的失败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。
这些改进方案,有的关于舰船龙骨的力学结构,有的关于火药配方的燃烧效率,甚至还有关于制造局内部管理流程的优化建议。
但所有人都只看到了一个老幕僚,在做着琐碎的文书工作。
制造局的主事官张大人,是个典型的科举出身官员,对这些机器图纸一窍不通。
他只负责每天给陈伯安送去茶水和饭食。
“陈先生,您何必如此劳累?曾帅让您整理,您随便分类即可,何必耗费心力,在这些废纸上写写画画?”张大人不解。
陈伯安笑道:“张大人,这些图纸不是废纸。它们是银子,是舰船,是国运。它们只是暂时沉睡了。”
张大人摇摇头,只觉得陈伯安是清流的臭毛病犯了,喜欢故作高深。
他将陈伯安的批注视为无用功。
“您老人家也快告老还乡了,早些办完交接,回家享福才是正道。”
陈伯安听罢,也只是微微一笑,继续埋首于图纸之中。
他知道,在这些人眼中,只有“做官”才是正道,而“实学”永远是末流。
这正是他心灰意冷的原因。
他将所有整理好的图纸,用麻绳捆扎好,整齐地堆放在档案室的一角。
他给曾国藩留了一封简短的信,说明了档案整理完毕,自己明日一早将启程回乡。
“我一生所学,皆在此处,只是无人能识。”陈伯安走出档案室,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铁锈味的空气。
他已经彻底放下了。
归隐山林,著书立说,或许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
当晚,陈伯安回到藩署,向曾国藩辞行。
曾国藩握着他的手,眼中充满了不舍与愧疚。
“伯安啊,你之才,实乃国家栋梁。为师知道,是为师耽误了你。但请你相信,你留下的这些东西,终有一日,会绽放光芒。”
陈伯安点头:“学生只希望,恩师能保重身体。”
次日清晨,一辆简朴的马车,载着陈伯安和他的两箱书,悄然离开了江宁藩署。
他没有惊动任何人,甚至没有去制造局告别。
他不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让他付出半生,却又让他心灰意冷的地方。
04
就在陈伯安的马车沿着官道向西行进时,数千里外的天津,直隶总督府,正陷入一场焦头烂额的危机。
李鸿章,这位曾国藩最得意的门生,此刻正面临着一个关于洋务的重大技术障碍。
李鸿章正在全力筹办北洋水师和天津机器局。
他从德国定制了一批最新的连发枪,并计划在国内仿制子弹壳和火药。
然而,在仿制子弹壳的冲压机床时,遇到了致命问题。
“中堂大人,这已经是第三台报废的机床了!”机器局的总办焦急地禀报。
“德国人提供的图纸我们完全照搬,材料也是最好的瑞典钢,可每次冲压到第三百发弹壳时,冲压机的关键部件——那个‘承力轴’,总是断裂!”
李鸿章的眉头紧锁。
这批连发枪是北洋水师的未来,如果子弹跟不上,一切都是空谈。
“请德国工程师来看了吗?”
“看了,他们也说不清楚,只说是我们操作不当,或者材料不纯。”总办无奈地回答。
李鸿章知道,这肯定是德方在图纸上留了一手,关键技术没有完全公开。
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恩师曾国藩。
论对机器局的理解和经验,曾国藩是开山鼻祖。
李鸿章立刻提笔,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函,详细描述了冲压机床“承力轴”断裂的问题,请曾国藩指点迷津。
信件快马加鞭,送往江宁。
与此同时,李鸿章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,派人前往江南制造局,索取关于“冲压机床”和“连杆受力”的所有档案和图纸。
他认为,既然是仿制洋人机器,江南制造局肯定也有过类似的失败经验。
天津机器局的两位技术官员,带着李鸿章的命令,急匆匆地赶到了江宁。
他们抵达时,陈伯安刚刚离开。

05
江宁藩署。
曾国藩收到了李鸿章的急信,心中也犯了难。
冲压机床的承力轴断裂?
这确实是个棘手的力学问题。
他自己虽然懂一些格物之理,但要立刻提出解决方案,却也无从下手。
他想起昨日陈伯安的辞行,心中一动。
陈伯安对这些“奇技淫巧”的研究,比自己深入得多。
“快去制造局,把陈伯安整理的那些图纸都拿过来,尤其是关于连杆、轴承受力的那部分!”曾国藩吩咐下去。
制造局的官员立刻将陈伯安整理好的图纸送了过来。
李鸿章派来的两位技术官员也同时赶到,他们也需要查阅这些资料。
在藩署的书房里,三人展开了厚厚一叠图纸。
大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洋文和线条,两位技术官看得头晕眼花。
“中堂大人要我们找的是关于‘承力轴’结构改进的资料,可这些都是失败的图纸啊。”一位官员抱怨道。
曾国藩示意他们继续翻找。
就在这时,另一位官员翻到了陈伯安批注的那张“蒸汽机活塞连杆”的草图。
这张图纸本身是制造局早年仿制失败的产物,但空白处密密麻麻的墨迹,引起了官员的注意。
“这是谁写的批注?字迹倒是清秀。”官员疑惑道。
曾国藩接过图纸,定睛一看。
正是陈伯安的字迹!
他看到图纸角落的那段话:
“此处应为应力集中点。连杆断裂,非材之过,乃几何结构之误也。若将连接处倒圆角,并适当增加厚度,可有效分散拉应力。”
曾国藩的心脏猛地一跳。
陈伯安在这段批注中,清晰地指出了连杆断裂的根本原因——几何结构。
这与李鸿章在信中描述的“承力轴断裂”问题,如出一辙!
他立刻让技术官员仔细阅读这段批注。
官员们一开始不以为意,但当他们用尺子仔细测量了图纸上的结构,并对照李鸿章信中的描述时,他们震惊了。
“这……这简直是神来之笔!天津机器局的问题,正是这个‘应力集中’!我们一直以为是材料强度不够,没想到,只需要改变几何形状,就能解决!”技术官员激动得声音颤抖。
曾国藩看着那张图纸,心中五味杂陈。
他知道,陈伯安不仅解决了天津的燃眉之急,更重要的是,他展现了对近代实学超前的理解。
他辅佐自己半生,自己未能给他一官半职,他只能在临走前,用这种方式,留下自己的智慧。
“快!去追陈伯安!他今日一早,应该刚出城门不远!”曾国藩急声吩咐。
然而,送信的侍卫很快回报:“回禀曾帅,陈先生的马车已经走了两日路程,正在往安徽方向赶去,此时已过了三百里官道,恐怕难以追及。”
曾国藩脸色铁青。
他错过了一个挽留这位绝世人才的最后机会。
但紧接着,他看向了两位李鸿章派来的技术官员。
“你们立刻带着这张图纸,以及所有陈伯安批注过的资料,连夜赶回天津!务必一字不漏地禀告李鸿章!”
“是!”两位官员如获至宝,立刻带着资料,冲出了藩署。
曾国藩回到书房,坐下。
他知道,李鸿章看到这些批注后,一定会明白陈伯安的价值。
他提笔,亲自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回信。
他没有直接回答李鸿章的问题,而是重点描述了陈伯安此人,以及他整理图纸时所做的批注。
这封信的内容,比任何举荐信都要有力。
当晚,李鸿章正在天津总督府内,为机床断裂的事情彻夜难眠。
深夜,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响起。
“中堂大人,江宁急报!”
李鸿章拆开信件,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曾国藩手书的那段话:
“此人对于洋务运动或有大用。”
李鸿章心中一震,立刻将信件展开阅读。
他很快读到了曾国藩关于陈伯安其人,以及他在图纸上批注的描述。
李鸿章的眼神,从最初的疑惑,变成了震惊,最后变成了狂喜。
他立刻召见了两位技术官员,让他们详细解读了陈伯安关于“应力集中”的批注,并让他们展示了所有带批注的图纸。
李鸿章是实干家,他一眼就看出了陈伯安见识的超前性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,这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“钥匙”。
他意识到,自己面对的,是一位真正精通近代科学原理的奇才。
而这位奇才,此刻正在归隐的路上。
李鸿章没有片刻犹豫,他立刻铺开宣纸,蘸墨,连夜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长长的致函。
这封信,将彻底改变陈伯安的命运。
06
李鸿章的笔触带着急切,但字里行间,是身为晚清实干家对人才的极度渴求。
他没有客套,直接切入了对陈伯安的评价。
“恩师钧鉴: 弟子拜读恩师来函及附件图纸,心潮澎湃,夜不能寐。
陈伯安先生之才,弟子以往只闻其名,以为不过是深谙典籍之清流幕僚。
然观其批注,方知大错特错。 先生并非一般幕僚,而是深得‘格物致知’真谛,通晓西学原理的实干之才!
他所言之‘应力集中’,正是弟子在天津机器局所遇困局的症结所在。德人图纸讳莫如深,我等苦思不得其解,而先生仅凭一张废弃图纸,便能一语道破玄机,可见其学问已臻化境。
恩师!今日之中国,缺的不是那些只会高谈心性、空议国是的清流!缺的正是陈伯安先生这般,能将实学与国事结合,能解决实际问题的‘洋务’人才!
他二十年未得一官半职,并非其才不立,而是其才太超前,不为守旧者所容。
弟子深知,恩师晚年,求稳为上。但洋务运动,刻不容缓。机器局、水师、铁路,皆需此等精通实学,又深知国情的智囊。
若任由陈先生归隐,实乃朝廷之巨失,洋务之大憾! 弟子斗胆,请恩师务必想方设法,将陈伯安先生挽留。
弟子愿以天津机器局总办(正三品)之职相邀,另加北洋水师顾问虚衔,许其不必参与繁琐官场应酬,只负责技术指导、图纸校核、人才培养等实事。
恩师,请代弟子向陈先生致意,此番并非请他入仕,而是请他出山救国!唯有此等大才,方能为我洋务事业,拨开迷雾,少走弯路。
弟子已安排快马,星夜兼程送此函至江宁。恳请恩师三思,勿使国之重器,埋没于乡野之间!”
李鸿章放下笔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他知道,曾国藩最重情义,也最重国事。
这封信,既是恳请,也是激将。
他将信件封好,盖上总督大印,立刻派出了八百里加急的快骑。
当李鸿章的信抵达江宁时,已是第三日清晨。
曾国藩收到信件,展开阅读。
李鸿章开出的条件,让他心惊。
正三品的机器局总办,这已经是当时洋务体系中,极高的实权职位。
更重要的是,李鸿章明确承诺,让陈伯安“只负责实事,不参官场”。
这完全契合陈伯安的性情。
曾国藩深知,李鸿章的这份诚意,是真心实意。
他看着信件,心中挣扎。
陈伯安已经归乡心切,自己若是以“恩师”之名,强留他继续为国效力,是否过于残忍?
他已年近六十,理应颐养天年。
但李鸿章信中那句“国之重器,埋没于乡野之间”,像一记重锤,敲击着曾国藩的心房。
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创办制造局时的艰难,想起了多少钱财、多少心血,因为技术上的一个微小失误而付诸东流。
陈伯安的价值,远超一个三品官职。
他能为国家节省的,是无数年的光阴和数百万两白银的浪费。
曾国藩下定决心。
他不能让陈伯安走。
07
曾国藩立刻召集了最得力的侍卫和快马。
“沿着官道,追!务必在陈伯安抵达安徽老家前,将他请回江宁!”
他知道,陈伯安是清高之人,硬性命令只会适得其反。
曾国藩决定,亲自写一封信给陈伯安,但信中不提官职,只谈“天下大局”。
他提笔,语气亲切而沉重:
“伯安吾弟: 自你辞行后,为兄思之再三,心绪难平。
你我相交二十载,情同手足,你之才学,为兄心知肚明,未能让你早日入仕,实乃为兄的愧疚。
然,为兄昨日收到李鸿章来函。他在信中,对你留下的‘应力集中’批注,赞不绝口,奉为圭臬。
伯安,你二十年所学,并非无用,而是等待一个能真正赏识你,并能为你提供施展抱负平台的人。
李鸿章,正是此人。他务实、果决,正大力推行洋务,急需你这样精通实学的智者。 为兄不愿以恩师之名,强留你。
但为兄恳求你,以天下苍生为念,暂缓归乡之行。 你可先来天津,与李鸿章一见。若你认为他所言非虚,所谋非小,你便留下。
若你依旧心灰意冷,不愿再入世,为兄绝不强求,并亲自为你饯行。
为兄知道,你厌恶官场纷争,李鸿章已许诺,让你只做纯粹的技术实务,不受官场掣肘。 你此行,是去天津,为天下实学正名,而非为一己私利求官。
望伯安三思,速归江宁。为兄等你。”
曾国藩将信件交给侍卫,并附上了自己的私人腰牌,以示事态紧急。
侍卫们骑着快马,沿着陈伯安归乡的路线,星夜追赶。
三天后,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一处小客栈里,侍卫们终于追上了陈伯安。
陈伯安正坐在客栈里,喝着粗茶,准备第二天进入老家地界。
当他看到曾国藩的私人腰牌,以及那封语气沉重的亲笔信时,他感到意外。
他打开信件,逐字逐句地阅读。
当他读到李鸿章“赞不绝口”和“深得格物致知真谛”时,他那颗已经平静的心,再次泛起了波澜。
二十年的埋没,二十年的不解,仿佛在这一刻,得到了迟来的回应。
最打动他的,不是李鸿章开出的官职(他甚至不知道李鸿章开出了三品官),而是曾国藩信中的那句:“你此行,是去天津,为天下实学正名。”
他并非真的厌倦了为国效力,他只是厌倦了在浮夸的官场中,做那些无用的空谈。
他整理图纸时,曾想过,如果自己的这些见解能被人看到,能真的帮到洋务事业,那该多好。
现在,机会来了。
他深吸一口气,站起身,对侍卫说:“请告知曾帅,伯安愿往天津一行。”
08
陈伯安没有回江宁,他直接在侍卫的护送下,改道北上,直奔天津。
他知道,时间宝贵,李鸿章肯定急需人才。
十日后,陈伯安抵达天津。
他没有先去李鸿章的总督府,而是直接去了天津机器局。
他想先看看,李鸿章的洋务,到底做得如何。
机器局内,一片繁忙。
陈伯安看到,技术人员正在按照他图纸上的批注,对那台冲压机床的承力轴进行几何结构的修改。
当他走进车间时,李鸿章已经得到了消息,立刻快步迎了出来。
李鸿章比陈伯安年轻近二十岁,但他身上散发着强烈的锐气和务实精神。
“陈先生!久仰大名,今日终得一见!”李鸿章语气恭敬,没有一丝总督的架子。
陈伯安拱手:“中堂大人客气了,老朽不过一介幕僚,不敢当此大礼。”
“先生不必谦虚!您那关于‘应力集中’的几行字,胜过我机器局数十位匠师数月的苦思!”李鸿章直言不讳,眼中充满了对人才的欣赏。
李鸿章没有急着提官职。
他知道,对陈伯安这样的人,功名利禄已是浮云,能够施展抱负,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
“陈先生,请随我来。”
李鸿章带着陈伯安,参观了机器局的每一个车间,详细讲解了北洋水师的规划,以及他对铁路、电报等新事物的理解。
他发现,陈伯安的提问,总是能直击核心,且能提出更优化的方案。
在谈到海军轮船的煤耗问题时,李鸿章抱怨说,洋人的蒸汽机虽然动力强劲,但煤炭消耗巨大,大清根本负担不起。
陈伯安沉思片刻,说:“煤耗大,除了机器效率问题,还有船体设计。船体若能更符合流体力学,减少阻力,自可节省燃煤。”
“流体力学?”李鸿章不解。
陈伯安立刻在桌上画了一张简图,解释了船体水下部分形状对航速和阻力的影响。
李鸿章豁然开朗,当即拍案:“先生之学,真是开阔眼界!我已向恩师承诺,特聘先生为天津机器局总办,兼任北洋水师技术顾问,正三品!俸禄按照最高规格,并且,先生只负责实务,官场上的应酬,一概不必参与!”
陈伯安听到官职,依旧面色平静。
他看着李鸿章,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,眼中没有一丝傲慢,只有对实学的尊重和对国家的担当。
“中堂大人这份诚意,老朽心领了。”陈伯安终于点头,“老朽愿意留下。但老朽只求一事。”
“先生请讲!”
“老朽不需要三品官职,也不需要那些虚衔。”陈伯安语气坚定,“老朽只愿以‘机器局技术总教习’的名义留下。老朽要做的,是培养真正懂得‘格物致知’的实学人才,而不是去做一个官僚。”
李鸿章震惊了。
他从未见过有人拒绝三品高官,只求一个技术教习的虚职。
但他很快明白了陈伯安的心意。
陈伯安要的,是纯粹的、能改变中国的实学。
“好!我答应先生!技术总教习,地位等同总办,但只管技术,不问政事!”李鸿章兴奋地握住了陈伯安的手。
陈伯安,这位辅佐曾国藩半生未得一职的幕僚,终于在李鸿章的力邀下,找到了他真正的战场。
他的复出,标志着洋务运动中,一个全新的、注重科学原理的时代即将开启。
09
陈伯安出任天津机器局技术总教习,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,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。
他首先做的,不是改进机器,而是改进人。
“机器之利,在于其精;而人之利,在于其知。”陈伯安在机器局内部开办了一个小小的“实学讲习所”。
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关于力学、几何、材料学、流体力学的知识,系统地传授给机器局的年轻技术员和学徒。
这些知识,是从前技术人员在仿制中摸索不出来的“黑箱”。
陈伯安用清晰的逻辑和严谨的算术,将这些原理彻底解构。
“以前我们造船,只知道龙骨要粗,船体要大,却不知道阻力是怎么产生的。”一位年轻的技术员激动地说,“现在我们知道了,船头要以‘抛物线’的形状入水,方能破浪前行!”
陈伯安还亲自主持了多项关键的改进工作,他还坚持进入讲习所的人,必须通过算术和制图的考试,彻底打破了传统官僚体系对人才的限制。
他的工作成效斐然。
仅仅一年时间,天津机器局在技术上的进步,就超越了江南制造局过去三年的成就。
李鸿章对陈伯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“恩师,您看,陈先生这哪里是来做教习的?他分明是来做‘洋务之师’的!”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,毫不掩饰对陈伯安的赞誉。
陈伯安也感到,这才是他二十年来真正想做的事情。
他不再需要应付官场的尔虞我诈,他的价值,完全由他解决的实际问题来衡量。
他每日与机器、图纸、学徒为伴,他的白发,似乎也因这份热忱而焕发了新的光彩。
10
陈伯安在天津机器局的工作,持续了整整十年。
他以一人之力,为北洋水师和机器局培养了一批精通西学、懂得实务的骨干力量。
他修订和完善了大量的机器图纸,使中国的仿制技术,从“照猫画虎”提升到了“知其所以然”。
他虽然拒绝了所有的官职,但他所享有的尊敬和权力,远超许多三品大员。
在洋务运动的史册中,陈伯安的名字鲜少出现在正式的官员名单上,但他却是李鸿章在技术决策上,最依赖的“幕后大脑”。
光绪年间,陈伯安病逝于天津。
李鸿章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。
墓志铭中,李鸿章写道:
“陈公伯安,辅文正公(曾国藩)二十年,不慕功名,独精格物。尝谓:‘国之强盛,在器械之精,器械之精,在理学之明。’公之学问,超越时代。晚年入我幕府,十年间,为北洋机器局奠定实学之基。公虽无品级,然其功绩,当永载洋务史册,不输封疆大吏。”
曾国藩听闻陈伯安逝世的消息,老泪纵横。
他曾遗憾自己未能提携老友,却欣慰于陈伯安最终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。
曾国藩对人评价道:“伯安之才,若在承平之世,或许只是个清流。但在今日,他那份对实学的执着,恰恰是救国之药。幸好有李鸿章,能识得真金,没有让国之重器,埋没于乡野。”
陈伯安的故事,成为了晚清官场上一个独特的注脚:
在一个注重人脉和资历的时代,真正的实学与才能,终究会被务实的领袖所发掘。
他用二十年的等待,换来了十年的辉煌。
他用一张废弃图纸上的几行批注,证明了自己被埋没的价值。
实学兴国,人才不朽。
创作声明:本文为虚构创作,请勿与现实关联。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,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,仅用于叙事呈现,请知悉。
网上配资账号,股票配资平台,股票配资交易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